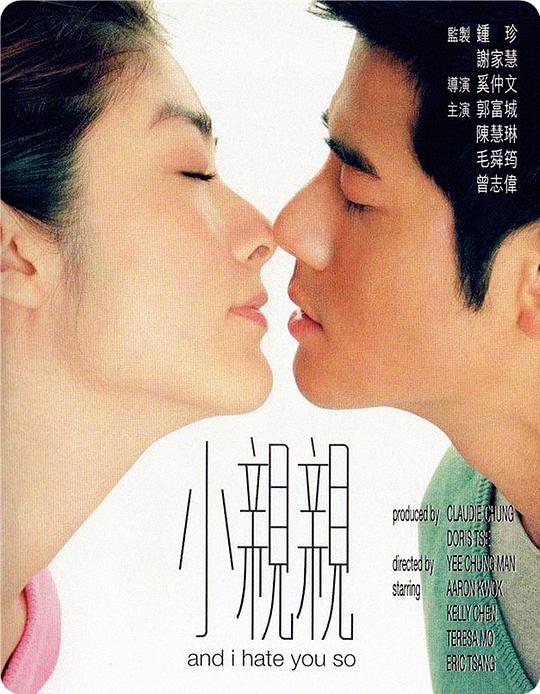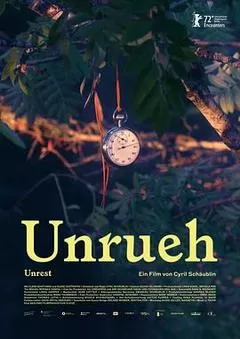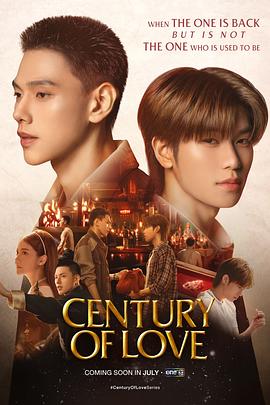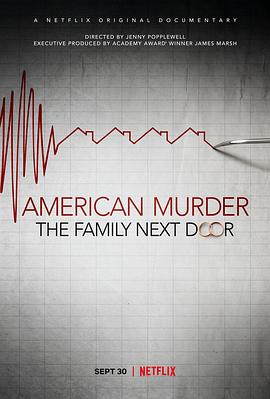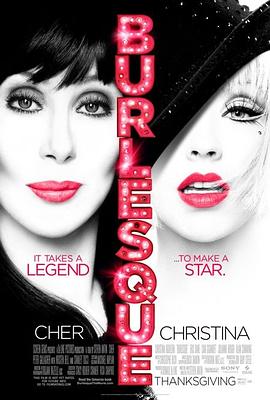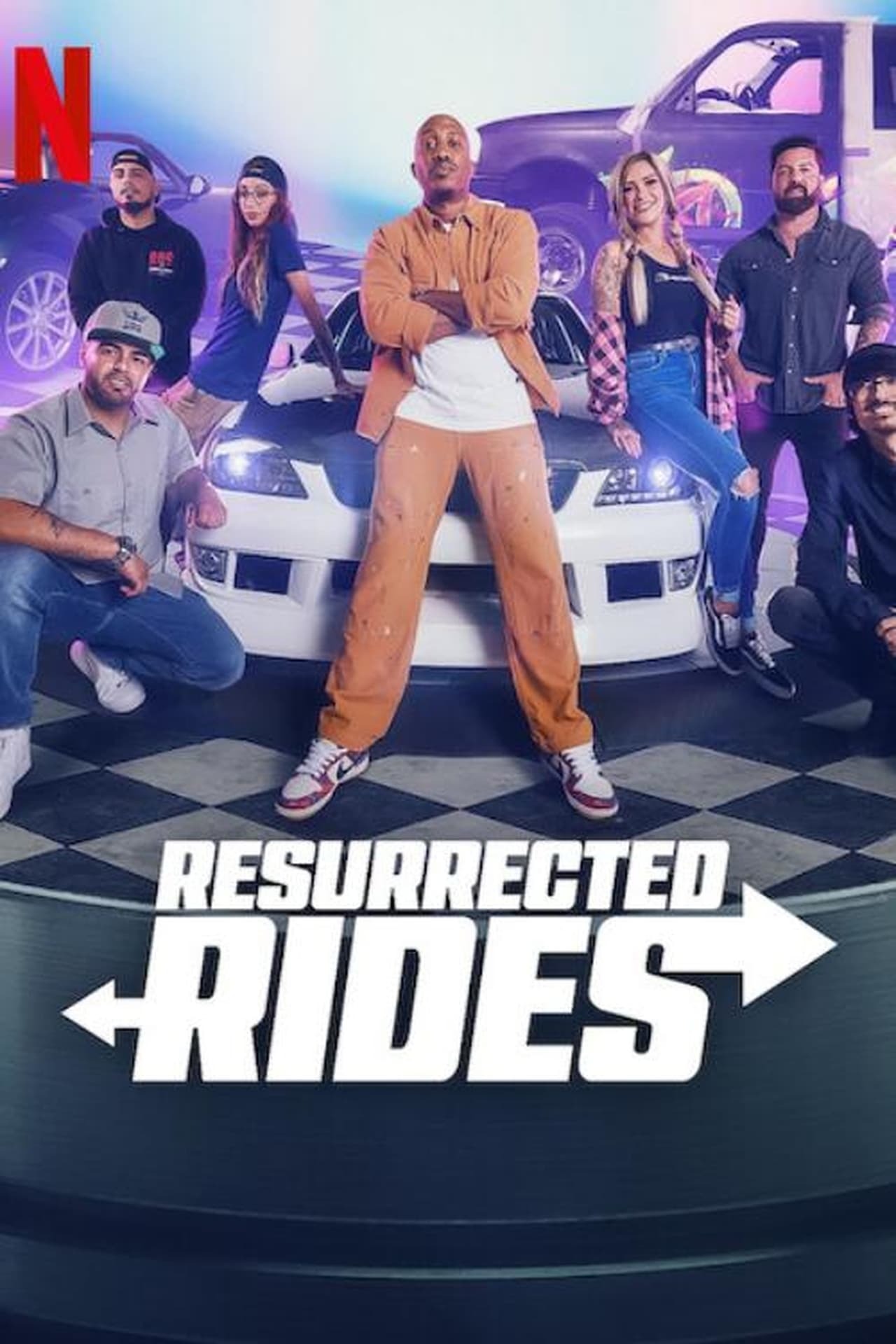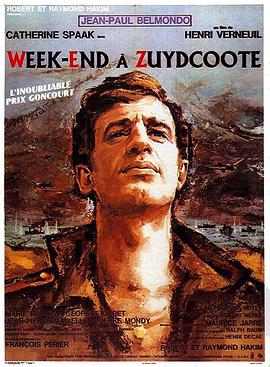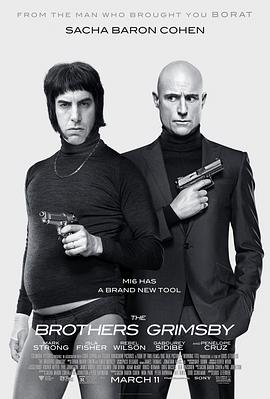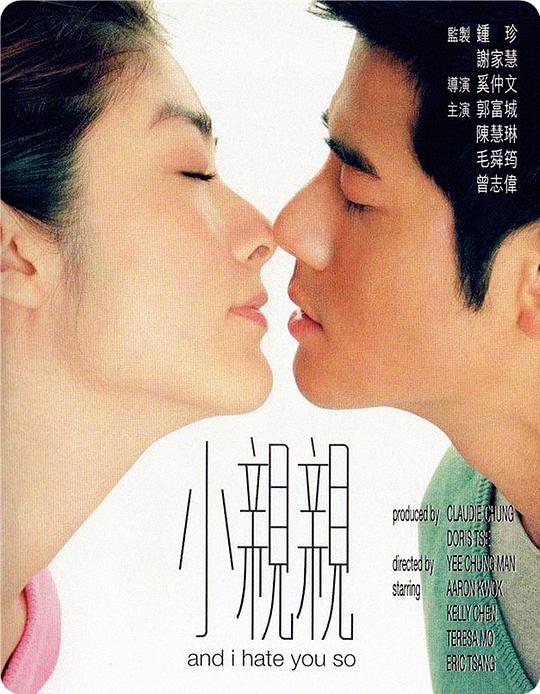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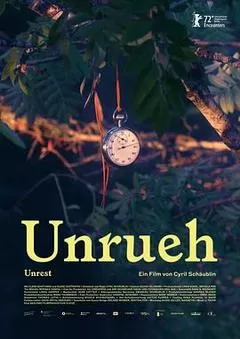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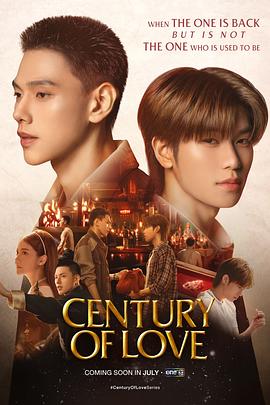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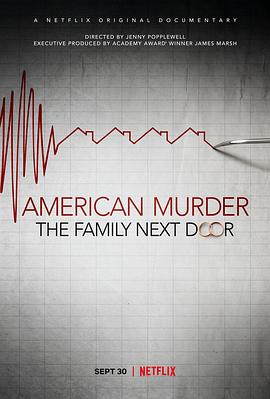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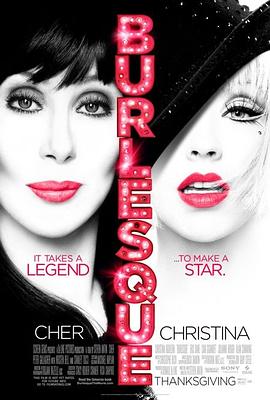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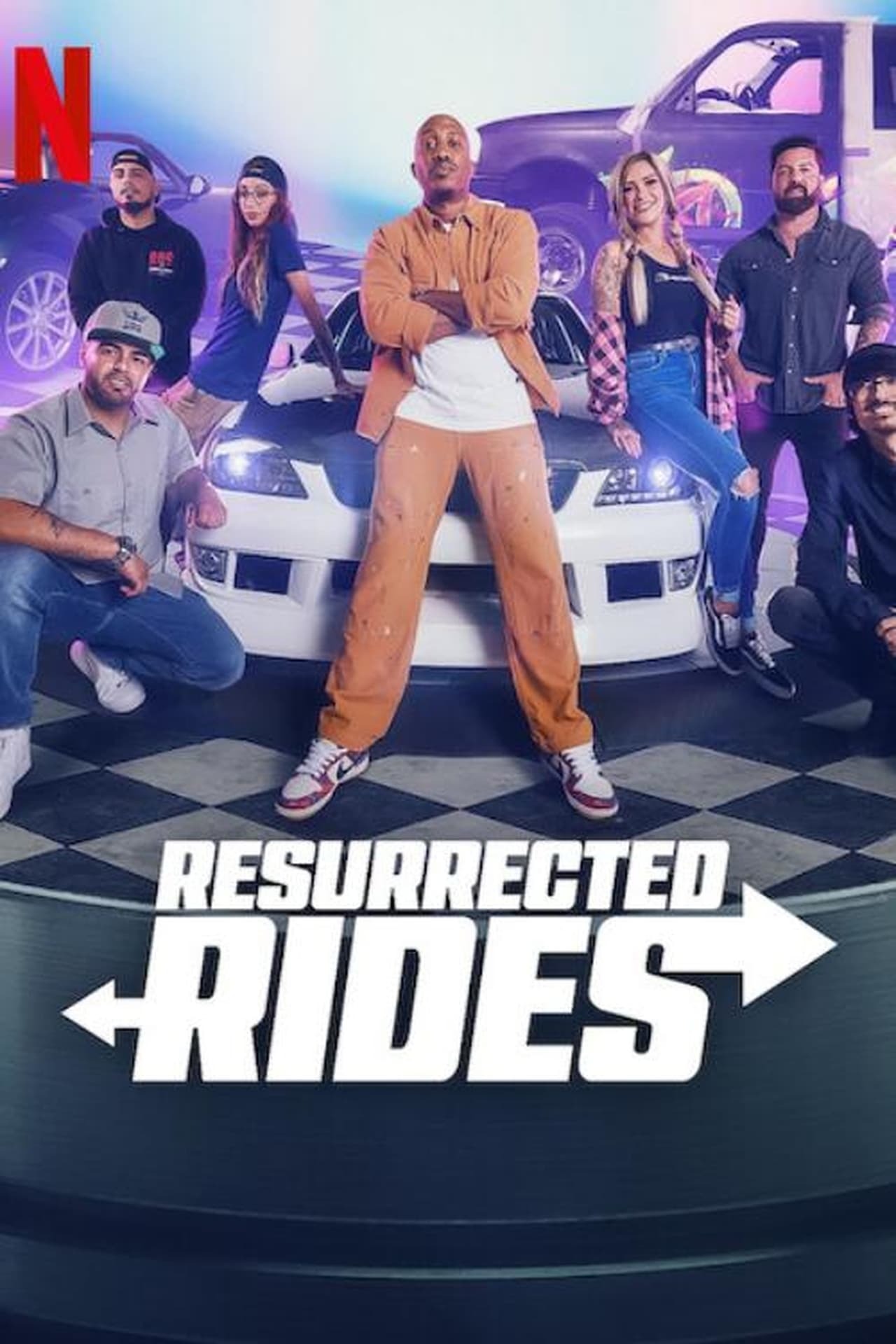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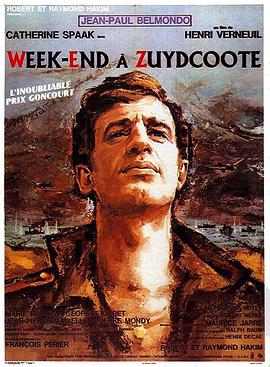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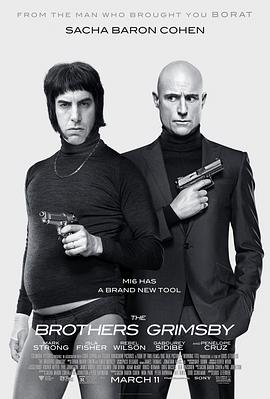





【导读】随着特朗普政府在2025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中传递出“退回西半球”的清晰意图,并抛出“C5”(美中俄印日)、“G2”(美中)等新大国体系论调,一些分析认为美国将要全面战略收缩并承认中美共治,从而乐观地将其视为世界走向和平的信号。且不说这种分析是否言过其实,我们首先还是要看清其战略内核。就内核而言,特朗普政府将解决国内问题放在首位,并强调重振以白人基督教传统为核心的美国文化。如果说特朗普政府的第一任期旨在回应“美国怎么办”,那么第二任期则升维至一个更加根本性的问题——“我们(美国人)是谁?”
在这个问题上,明眼人都看到了特朗普政府背后的“亨廷顿回响”。亨廷顿以“文明冲突论”闻名于世,人们往往从全球视角看待其理论。然而本文却点出其理论的美国内部根源,进而揭示亨廷顿既担忧西方内部主体性丧失、又焦虑西方霸权优势地位不保的双重思维联动性:一方面,美国及西方内部的认同危机,促使其借“文明冲突论”制造“敌我对立叙事”,试图通过树立外敌来重塑内部团结;另一方面,美国及西方阵营的实力衰退,迫使其基于“文明理由”收缩范围、保存实力,并挑动非西方国家相互冲突以实现分而治之。
这两方面的计算,隐隐地影响了美国的战略调整——以“美国优先”为核心、以“保守西方”为底盘,在对内修复、自我重振、守住势力范围的同时,在全球实施选择性收缩、相机性霸权、策略性挑动的三重行动布局,既欲“鹬蚌相争渔翁得利”,又可集中力量瞄准东方。就此而言,前述乐观的看法可能误解了特朗普宣称“中美共治”的真正目的,更误判了美国当前的政策取向。对此,有必要保持足够的冷静和清醒。
本文原载《读书》2025年12期新刊,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读者参考。
亨廷顿的幽灵,还是“西方”的重建?
张佳俊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
一
欧美世界正在经历一场历史性的重组。和历史上的情境相似,新一轮的重组,既有合,也有分。合表现在,人们心照不宣地唤醒“西方与非西方”的二元思维,不断刺激群体意识,试图实现某种整合;分表现在,重组是在一种高度分裂、撕扯乃至濒临瓦解的状态中展开的。如此悖反的场景,不免让人疑惑:这到底是意味着“西方”的重建,还是意味着西方的“终结”?其中最戏剧性的一幕,莫过于美国副总统万斯在2025年西方情人节这一天,公开批评亲密盟友:“我最担心的欧洲的威胁,不是俄国,不是中国,也不是任何其他外部势力。我担心的是内部威胁。欧洲正背离一些最基础的、本与美国共享的价值观。”面对出乎意料的当头棒喝,欧洲主流界不出所料地集体惊诧、义愤填膺却又无可奈何。毕竟,随着特朗普第二次入主白宫,保守力量的全面反攻渐成烽火连天之势,西方内部的“主义之争”及背后的“生意之争”已在所难免。
英国《卫报》称“万斯在慕尼黑的演讲揭示了跨大西洋联盟的崩溃”(来源:英国《卫报》)
在所难免则必有前因。2024年秋天,我随学术交流团队访问西欧与东欧,就近观察俄乌战争后、美国大选前的欧洲社会,一连串疑问就曾涌入脑海:一个看似“统一”的欧洲何以如此散装?一个高谈“正确”的欧洲何以自相矛盾?一个自诩“天堂”的欧洲何以陷入停滞?连一个旁观者都感觉不妙,欧洲的明白人想必也心里有数——只是真正的明白人可能不占主流。在我当时所见的、有过交流的欧洲人中,多数精英都预感美国政坛即将倒蓝翻红,欧洲的严峻形势将更加严峻,因而开始焦虑地讨论接下来该怎么办。精英们的短期预见能力倒也不差,但其基于某些“既定正确”而形成的认知框架,往往有种自我设限的味道。除了极少数垂垂老矣的清醒者外,许多人自信欧洲走在正确道路上,往往把当下局面的症结归咎于外部,而很少从欧洲内部、从他们自己身上找原因——这与一些街头百姓毫不掩饰对己国政府的失望、对主流精英的鄙夷以及对社会变质的忧虑形成鲜明对比。或许也是因为这样,万斯的话才让他们猝不及防。
美国大选前的东欧:左图为2024年美国大选前一周,匈牙利街头张贴的主流媒体Mandiner分析大选形势的海报;右图为当时匈牙利布达佩斯一栋楼房上挂出支持特朗普主张、直言“哈里斯被炒”的标语(来源:作者摄)
然而,万斯之言并无新意。他不过是重述了过去几十年美国保守派的一贯表达,而且话里话外都带着隐隐的历史回音。听懂的人大概都会想起一个故人,那就是美国知名保守派学者塞缪尔·亨廷顿,也会想起他那引发巨大争议的“文明冲突论”。尽管如今距离亨廷顿发表《文明的冲突?》、后又出版《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新华出版社二〇一〇年修订版,下引此书,只注页码)已过去三十多年,但争论并未停歇。面对后亨廷顿时代四处起火的世界,一些人暗叹亨廷顿未卜先知,一些人批判这是自我实现的谶言。而亨廷顿的精神继承人们——美国民族主义保守派则念兹在兹,终于等到重新掌权、改天换地的这一天,于是便有了万斯的忧心与亨廷顿的幽灵的遥相呼应。
如此看来,要理解当前西方内部同时存在的裂解与整合,评估西方自我修复的可能与不可能,还是有必要重读亨廷顿。
二
过去三十多年围绕亨廷顿及其“文明冲突论”的讨论,多聚焦于国际政治层面。多数批评者都把矛头对准全球维度的“文明冲突论”,而非美国和西方维度的“文明冲突论”,进而不可避免地产生一些解读,例如认为“文明冲突论”是一种主张文明冲突乃至战争的理论——继亨廷顿之后西方出现的各类“冲突论”变种,也确实受到这一理论的深刻影响。然而,重读亨廷顿的文本,可以发现其中虽有对国际冲突现实及趋势的事实性评估,却并非草率地主张文明冲突。就其理论全貌而言,亨廷顿精心建立“文明冲突论”框架,首要目的显然不是简单鼓吹文明冲突乃至战争。也是注意到了世人的误解,他特意强调:“文明的冲突是对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胁,而建立在多文明基础上的国际秩序是防止世界大战的最可靠保障。”(第291页)
从美国和西方的维度看“文明冲突论”,或许更容易读懂亨廷顿的心思。作为美国新保守主义的代表人物,亨廷顿最初的问题意识不来自国际,而来自美国国内。他的出发点不是对所谓文明冲突的忧惧,而首先是对美国本土危机的担忧,以及由此延伸的对整个西方内部分裂的焦虑。
今天,当左翼推动的“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彩虹运动”“DEI运动”等席卷欧美并与右翼形成尖锐对峙,以至于引发特朗普政府第二任期排山倒海般的反击浪潮时,人们不必惊奇,因为这场“文化战争”早在1960年代就打响了,到了“文明冲突论”诞生的20世纪末期,已经势如水火。少年和青年亨廷顿曾亲历美国工业化和经济发展最迅速、大量外来移民归化美国“大熔炉”的时代,中年亨廷顿则目睹美国民权运动风起云涌和多元主义弥散的时代,而接近古稀之年的亨廷顿眼睁睁看着美国“大熔炉”失败,更伤感于白人主流文化被文化多元主义解构、稀释甚至压抑的无奈。面对一个社会文化冲突加剧的美国,一个少数群体平权成为“政治正确”而谈之色变的美国,一个在保守派看来“礼崩乐坏”的美国,亨廷顿的愁绪可想而知。尽管起初他只谈全球文明冲突而回避内部敏感话题,但在后来回应外界批评时,他承认“文明范式对美国也有意义”。
不同肤色种族的美国人手持星条旗,他们心中的美国是同一个美国吗(来源:美国国家历史博物馆National Museum of American History)
在亨廷顿心里,源于欧洲的盎格鲁-新教文化及其政治社会价值观,是美国合众为一的立国之本。然而,随着生育率高且自带宗教文化认同的非西方国家移民大量涌入低生育率的欧美各国,西方尤其美国自然形成了种族多元化与认同多元化的双重结构。亨廷顿强烈感觉到,美国的国本被少数群体“要求政府赋予其特权”的平权运动冲击,一些欧美精英还“以多元文化主义的名义攻击美国对西方文明的认同,否认存在一个共同的美国文化,提倡种族、民族和亚民族的文化认同与分类”(第281页)。这就必然“激起美国内部的文明冲突”,导致“美国的分裂”。更让他不安的是,如果将来50%的美国人都变成拉美裔或非白人,而这些人又难以融入盎格鲁-新教文化,那时的美国就可能去西方化甚至去美国化,最终像另一个超级大国那样落入“历史垃圾堆”。(If Not Civilizations, What? Paradigms of the Post-Cold War World, Foreign Affairs, Vol. 72, No. 5, 1993)正是出于这种恐惧,亨廷顿后来在另一本书《我们是谁?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中,直言美国面临身份认同危机,并批判基于多元种族和多元文化的身份政治解构了美国特性,从内部瓦解了美国乃至西方文明。在这一点上,无论特朗普、万斯还是其他极右翼政客,都与亨廷顿共享同样的危机意识。他们组成所谓“民族主义保守派”,挑动和利用白人群体危机感,强调“血统美国人”(Heritage Americans)的纯粹性,把自己打造成美利坚民族“救世主”。他们宣扬美国民族主义,强调美国不只是理念(notion),而是有着共同历史和未来的民族(nation),这里的民族,主体就是欧裔白人。
美国右翼政治背后的“亨廷顿回响”
不独美国,欧洲尤其西欧的多元化浪潮也齐头并进,在文化、性别、移民、环保等领域甚至走得更远,更加偏离保守价值观,其内部同样处于文化冲突和利益矛盾的撕扯之中。就整个西方阵营而言,冷战后,没了苏联这个“最大对手”,原本高度捆绑的欧美同盟开始松动,不仅在重大国际问题上时有分歧,在文化价值层面也出现分殊。如此一来,整个西方世界普遍陷入自己反对自己的“文化战争”危机。于是,亨廷顿提出了“文明冲突论”的元问题——“我们是谁”,并强调“我们只有在了解我们不是谁、并常常只有在了解我们反对谁时,才了解我们是谁”(第5页)。
亨廷顿提出这个问题时,就预设了解决西方内部认同危机的方法论,那就是“区分敌我”的政治逻辑。他表面上说的是文化认同和文明冲突,对应的其实是政治认同和敌我冲突。这种从基督教一神教体系中衍生而出的二元对立逻辑,最有利于西方进行政治动员和力量整合。而融民族、宗教、历史、文化于一体的“文明”概念,要比其他概念更容易模糊西方内部矛盾、聚拢整体认同。由此可以理解,为什么亨廷顿要着重指出西方与非西方的“文明冲突”,进而呼吁美国重振盎格鲁-新教文化认同,强调西方国家共享基督教文明价值观。更可以理解,为什么他要论证西方文化的独特性,否定所谓“普世价值”的普世性。在他看来,许多西方精英像福山那样信以为真地鼓吹“历史终结”,一厢情愿地把西方价值推广成全球“普世价值”,不仅不利于西方自己维护内部认同,而且必然引起其他文明抵触,使西方陷入“他们”反对“我们”的“文明冲突”危机。(第277-288页)正是认识到普世价值不受欢迎而且“对世界是危险的”,他建议西方停止输出“普世价值”,甚至毫不避讳地警告美欧:“最为重要的是,认识到西方对其他文明事务的干预,可能是造成多文明世界的不稳定和潜在全球冲突的唯一最危险因素。”(第288页)
基督教对美国传统的深刻塑造:左图为第三任美国总统、《独立宣言》和《弗吉尼亚宗教自由法案》作者托马斯·杰斐逊剪贴自制的《新约全书》压缩版;右图为第六任美国总统、美国圣经协会副主席约翰·昆西·亚当斯总统在1837年送给孙女的一本德文圣经(来源:美国国家历史博物馆National Museum of American History)
从这个角度看,“文明冲突论”与其说是咄咄逼人的叫战书,不如说是用意精深的劝谏书。亨廷顿的用意,就是集中精力办好西方自己的事。这意味着西方必须克制普世主义的虚妄与对外干涉主义的傲慢,实施战略收缩。但如果只是为了解决内部认同危机,似乎还达不到让西方主动退却的程度。毕竟在实力层面,当时的西方阵营刚刚赢得冷战,而美国更是处于“巅峰时刻”,似乎再无对手。既然如此,为什么亨廷顿反其道而行之,劝美欧往后退呢?
三
问题就出在实力上。作为一位冷峻的现实主义者,亨廷顿当然不是因为爱好世界和平而规劝欧美克制。他深知国际较量始终围绕权力和利益展开。如果不是清醒意识到欧美世界已经历史性地进入衰落轨道,很难说亨廷顿不会另有激进主张。而对西方衰落进行诊断并提出重振西方的方案,正是“文明冲突论”的另一条主线。
文化背后是权力,权力背后是实力。亨廷顿明言:“文化在世界上的分布反映权力的分布。一个文明权力的扩张通常伴随着其文化的繁荣,而且这一文明几乎总是运用它的这种权力向其他社会推行其价值观、实践和体制。一个普世文明需要普世的权力。”(第72页)这里的“文明”,其实是“帝国”的代名词。他举了罗马、19世纪欧洲和20世纪美国的例子,正好对应罗马帝国、欧洲殖民帝国和美国主导的世界帝国。这三者代表着西方文明与权力的“辉煌”,也反映了西方从区域性帝国扩张为全球性帝国的历史过程。这个过程在近代加速,经过400多年上升期后,到1920年代左右达到顶峰——彼时西方殖民列强掀起了瓜分世界的狂潮。不过,自那以后,西方的实力和权势就在走下坡路了。一系列热战冷战之后,西方对世界的控制力大大下降,远不如从前。亨廷顿就此判断:“西方主宰天下的时代正在终结。与此同时,西方的衰落和其他权力中心的兴起正在促进全球本土化和非西方文明的复兴进程。”(第71页)而一旦失去绝对优势,西方霸权背后的帝国秩序便难以维持,如果继续霸道妄为,随之而来的将是非西方国家的反抗。以美国建构的世界帝国体系为例,冷战后的美国精英沉醉于胜利之中,非但没有收敛,反而滥用其帝国中心地位,频频对外发动战争、强推“普世文明”,还把全球化建立起来的世界经贸体系、创新体系、法律体系等公器私用化,肆意打压新兴国家,试图固化西方对广大后发国家的利益收割机制。这必然激起帝国疆域内的各种反抗。在美国越来越无力“平叛”却又不肯放弃霸权的局面下,国际冲突必然加剧,最终也会反噬其身,加快美国以及整个西方的实力消耗。
西方帝国政治的遗迹——夜幕下的罗马斗兽场(来源:作者摄)
对此,亨廷顿的建议是以文明认同为道、以利益交换为术,实现西方势力范围内的实力重建。“西方若想尽量减少损失,就必须在与其他社会打交道时,巧妙地将其经济资源作为胡萝卜和大棒来应用,以促进西方内部团结并协调其政策,既使得其他社会很难挑起一个西方国家反对另一个西方国家,又能够充分利用非西方国家之间的不同。西方推行这种战略的能力,一方面取决于它与挑战者文明发生冲突的性质和强度,另一方面取决于它获得摇摆文明的认同程度以及与摇摆文明建立共同利益的程度。”(第183页)换言之,即一边重建统一的基督教文明认同,弥合美国内部以及美欧之间的价值分裂和利益分化,强化以美欧为核心的同盟团结,避免因内部冲突而“自毁长城”;一边管控与非西方国家的冲突,避免卷入战争消耗自身,同时以利为饵拉拢摇摆国家,利用非西方国家之间的矛盾,防止其联合起来反对西方。这种内部整合与外部收缩的重建方案,不再执迷于全球性的普世帝国,而是重返区域性的西方帝国,目的就在于帮助美国及整个西方维护一种克制却有力的霸权地位。
从这个角度看近十年的美国,拜登政府和特朗普两任政府虽然政纲不同,但都有政策内倾和战略收缩的双重特点。代表自由派的拜登政府在姿态上依然延续全球主义路线、热衷意识形态输出,但其推行“中产阶级外交”、撤军阿富汗、加强美欧同盟、挑动大国竞争、刺激区域冲突等做法,都反映了既想避免美国国力透支,又想整合西方一致对外的意图,暗合亨廷顿的思路。特朗普政府则更体现亨廷顿原旨,一面与欧洲右翼形成大西洋保守主义乃至基督教民族主义阵线,联手对付左翼激进化浪潮,并利用种族、宗教等标签在全球开展敌我政治动员;另一面试图在地缘上重新整合西方,即退守西半球势力范围,对加拿大、墨西哥、丹麦格陵兰岛、巴拿马运河等提出不同程度的领土或控制权诉求,并以军逼利诱稳固其拉美“后院”。这种“领土帝国主义”冒天下之大不韪,实为亨廷顿“大西洋联盟”设想的扩大版,比文化价值观整合来的更加粗暴。特朗普政府也确实把经济“作为胡萝卜和大棒”来用,只是用得并不“巧妙”。它把派系私利裹进美国国家利益的外衣,将“美国优先”推演到“宁我负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负我”的程度,决意抛弃全球体系而打造以美国利益为中心的小圈子,对世界各国实施关税战等战略讹诈,即便对盟友也毫不客气,这显然超出亨廷顿的分寸感。这些激进做法,实际上把美国重建置于西方重建乃至世界秩序的重建之上,以后两者的失序为代价,来成全前者。这自然会拉大美欧裂痕,也打乱了亨廷顿期待的西方对非西方国家实施“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的基本布局。还要注意的是,无论哪派当政,所谓战略收缩都非全退而是半退,这种“选择性收缩”的对应着“相机性霸权”,即“霸权余威管用的事情任性办,霸权成本过高的事情看着办”,一旦实力重振,必行全球霸权。而且从内部看,左右两派无不为了党派利益而鼓动“文化战争”,结果是加剧美国乃至西方的撕裂。如果亨廷顿在天之灵看到这些人各怀鬼胎,把一盘大棋下成这样,不知道作何感想?
特朗普的西半球构想——“唐罗主义”(来源:New York Post)
不过,新一轮西方重组才刚刚开始。到底是保守派假借亨廷顿的幽灵,打乱格局重新分利,还是遵照亨廷顿的本义推动“西方”重建,尚需时间检验。眼下保守右翼对左翼思潮的清算反扑虽然破坏西方团结,但只要“西方与非西方”的敌我话语绵延不绝,这种重组就将持续,即便整合失败,也会不断催生新的冲突。对于我们来说,尤其要注意其为了自我重建而向外转嫁祸乱风险。因为“文明冲突论”不仅巧妙回避了西方内部更为本质的阶级矛盾,更在无形中遮蔽了世界帝国体系内更为根本的不平等问题。这不仅会误导认知,更容易助长两种西方惯用的手法:一是面对内患,不从自身找原因,而以树立外敌来实现内部团结;二是回避国际不平等的根源,借“文明冲突”的名义人为制造各种“敌我冲突”新陷阱,嫁祸他国或“策略性挑动”他国之间冲突。在此基础上,其未来战略纵有万化千变,不变的将是瞄准东方。对此,仅仅保持警惕或被动应对,恐怕不够。与过去几百年的世界秩序建构不同,这一次的世界秩序重构,时势已然巨变,历史主动权正在转移。就看我们能不能把握主动、顺势而为,不负人类历史的天命。
参考文献
[1] [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修订版),周琪等译,新华出版社,2010年版。
[2] 强世功:《文明终结与世界帝国:美国建构的全球法秩序》,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2021年版。